牌桌浮沉录:生死筹码间的命运翻牌
>在澳门最豪华的赌场VIP室内,
>我亲眼看见一位亿万富翁在半小时内输掉了全部家产,
>他微笑着站起身,优雅地整理领结,
>然后从容地从88层高的窗口跳了下去。
澳门的夜,是被金钱与欲望淬炼出的琉璃盏,盛满了流光溢彩的毒酒。永利皇宫的VIP室,“水舞”,便是这盏中毒液最浓郁的一滴。空气里雪茄的蓝雾与香水分子碰撞,底下是永不疲倦的人工湖音乐喷泉,轰响着奢靡的背景音。但在这里,所有声音都被厚重的羊毛地毯与天鹅绒壁毯吸走,只剩下筹码落下的清脆声响,一下,又一下,像心跳,更像倒计时。
李承业就坐在那张巨大的椭圆形巴卡拉水晶赌桌边。他不再是新闻图片里那个挥斥方遒的互联网新贵,熨帖的Brioni西装领口松开一丝,露出底下的疲惫。面前那座由各种面值筹码堆砌起的、曾引得侍者眼神都灼热起来的彩色小山,此刻已塌陷大半,只剩下几叠孤零零的紫色和零散的蓝色,在一片金黄与深黑的废墟上,显得格外刺眼。他的手指修长,指节分明,曾经在键盘上敲出过估值百亿的商业计划书,此刻却只是无意识地捻着一枚万元港币的紫色筹码,指尖泛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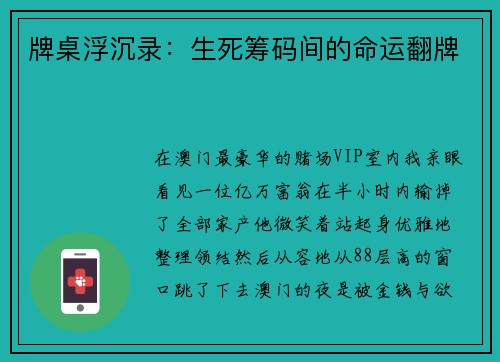
荷官是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白衬衫黑马甲,动作精准得像瑞士钟表。每一次派牌,每一次收走李承业推出去的筹码,眼神都没有丝毫波动。赌桌对面,分散坐着另外几位玩家,面目在吊灯散射的光线下有些模糊,更像是一团团移动的资本,偶尔投来的目光,带着审视,也带着一种见惯不惊的漠然。
又一局牌。李承业的底牌是一张黑桃A,明牌是一张红心K。他的眉毛几不可察地挑动了一下,像是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他推出了面前剩余的所有紫色筹码,那动作甚至带着点解脱般的决绝。“All in。”声音不高,有些沙哑,但在过分安静的房间里,清晰得吓人。
人。
对手,一个戴着金丝眼镜、一直在小口啜饮香槟的中年男人,几乎没有犹豫,跟着推了筹码。“Call。”
翻牌,转牌……公共牌面上花色杂陈,点数,点数微妙。空气凝固了。只剩下最后一张河牌,像断头台上的铡刀,悬在每个人的头顶。李承业的背脊挺得笔直,紧抿着唇,视线死死钉在荷官手中那张尚未翻开的牌上。
河牌落下。一张方块2。
荷官的声音平稳无波:“方先生顺子。”
金丝眼镜嘴角牵起一个微小的弧度,很快隐去。他开始慢条斯理地整理面前那座因吞噬了李承业所有筹码而愈发壮观的彩色山脉。
李承业定定地看着那张决定命运的方块2,看了足足有五秒钟。然后,他极其缓慢地靠向椅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预想中的惨白、冷汗或者崩溃的迹象。他甚至轻轻吁出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悟空德州他站起身。动作不疾不徐,先是抚平了西装前襟几乎不存在的褶皱,然后,双手抬起,熟练地整理了一下颈间那条深蓝色的爱马仕丝绸领结,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庄重。他对着桌边神色各异的众人,微微颔首,嘴角甚至勾起一抹极淡、极平静的微笑。那笑容里没有愤怒,没有不甘,只有一片虚无的温和。
没有人说话。只有香槟气泡在杯底破碎的细微声响。
他转身,迈步,走向那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澳门半岛最璀璨的夜景,灯火织成的锦绣山河,曾经似乎被他踩在脚下。服务员刚好端着托盘经过他身边,他顺手从托盘上取下一杯未动过的琥珀色烈酒,向对方致意,随即一饮而尽。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水舞”厅有一处延伸出去的观景露台,玻璃门悄无声息地滑开。他走了出去,夜风瞬间拂动了他额前的几缕发丝。他的身影在栏杆边停留了刹那,背对着室内的一切,面对着下方那片令人眩晕的光海。
然后,他单手在栏杆上一撑,整个人便轻飘飘地翻了出去。
没有惊呼,没有迟疑,甚至没有回头。
直到那道黑影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坠入下方那片由霓虹与黑暗交织成的深渊,室内才猛地爆发出第一声尖锐到变形的惊叫。酒杯摔碎在地毯上,闷响。有人踉跄着冲到窗边,徒劳地向下张望。
荷官停下了所有动作,僵在原地。那张年轻而冷漠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那是混杂着震惊与茫然的空白。
而我,一直远远站在角落阴影里的我,手里捏着的记录笔,“啪”一声,断了。掌心被断裂的塑料边缘硌得生疼,却毫无知觉。脑海里反复闪现的,只有他整理领结时,那双稳定得可怕的手,以及纵身一跃前,那抹平静得让人心底发寒的微笑。
窗外的澳门,依旧灯火辉煌,喧嚣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