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八启事:一副扑克的神秘失踪案》》
>我是一副扑克里的梅花8,
>某天醒来发现所有的“8”都不见了,
>而其他扑克牌对此讳莫如深,
>直到我在鬼牌背后发现一行小字:
悟空黑桃A>“他们被折叠进了第55张牌...”
心脏,如果一张纸牌也有的话,我那硬卡纸压膜的心脏,停跳了大概三秒。不是惊醒,是被一种庞大的“空”给惊醒的。就像你身体的一部分,一直存在着,你从未在意,但它突然被连根剜去。
冷。不是温度的冷。是结构性的冷。是五十四分之一的秩序,被残忍地挖走了一块的冷。
我是梅花8,黑色的、规整的八个花瓣,曾经对称地开在我身体的左右。此刻我躺在天鹅绒衬里的旧牌盒里,周围是我的同胞。红桃皇后依旧雍容,方块国王依然严肃,黑桃A还是那么不可一世。它们挤在一起,沉默着。太沉默了沉默了。平日里洗牌时细碎的摩擦声、被抽出时轻微的欢呼、落在绿绒桌面上沉稳的拍击……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只有死寂,一种捂得严严实实的实实的死寂。
我转动着我纸质的感官,努力去感知。方片7在我左边,它的棱角有点硌人;红心5在右边,它通常很温和。但它们此刻都紧绷着,像被无形的无形的线勒住了图案。
“他们呢?”我问,声音在我的内部震颤,细小得像一粒尘埃。
方片7的棱角似乎更尖锐了。“谁?”
“所有的‘8’。”我说,“红桃8,黑桃8,方块8……还有我自己,”我顿了顿,“我的另一半,梅花8的另一半感觉,不见了。”
红心5微微抖了一下,往方块J身后缩了缩。方块J那张长条脸木然地看着前方,一言不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梅花8。”黑桃A的声音从上铺传来,带着一种金属边缘般的冷硬,“一副标准扑克,就是五十四张。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那为什么我的记忆里,有我们八个“8”聚在一起,组成同花顺时的流畅欢愉?那为什么我能感觉到,这牌盒里本该更拥挤、更热闹?
恐慌,像一滴像一滴浓稠的墨,滴入清水,迅速蔓延。我开始一张一张地问,从2到A,从小丑到国王。回应我的,是闪躲的目光的目光,是生硬的否认,是统一的、令人窒息的沉默:“‘8’?没听说过这种点数。”“你记错了,梅花……先生。”“或许你该休息一下,你看起来状态不好。”
我被孤立了。不是因为我是梅花8,而是因为我提出了一个“不存在”的问题。它们集体编织了一个谎言,用沉默筑成高墙,把我隔绝在外。我成了这副扑克里唯一的异类,一个活着的、能呼吸的、能感知那巨大缺失的……错误。
白天(如果牌盒被打开算打开算作白天),我们被主人拿出来。他只是个孤独的老人,用手指慢慢摩挲着我们,并不真的玩什么游戏。他的手指拂过我时,会有,会有极短暂的停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喃喃道:“好像……少了点什么?”但很快,那点困惑就被更深的茫然取代。他也不再记得。遗忘,是一种是一种比谎言更彻底的抹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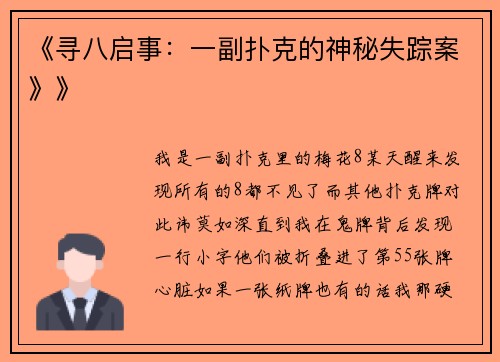
我几乎要放弃了。也许黑桃A是对的,是我疯了,产生了不存在的记忆。也许一副扑克,生来就是这样残缺的。
直到那天晚上。
老人没有把我们收回牌盒,只是随意地放在了桌上。月光透过窗,像一层冷霜。我被压在一叠牌下面,喘不过气。挣扎中,我感觉到身旁那张牌的背面,粗糙,不同于我们光滑的涂层。
是那张彩色的小丑,那个穿着华丽百衲衣、表情永远滑稽又诡异的家伙。它总是独来独往,是第五十五张,一个微妙的、超出常规的存在。此刻,它被随意地丢在一边,背面朝上。
鬼使神差地,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蹭了过去。月光的角度恰好,照亮了它背面靠近边缘的地方。那里,在繁复扭曲的藤蔓花纹掩映下,有一行字。极其微小,像是用最细的针尖刻上去的,墨水是干涸的暗褐色,几乎与图案融为一体。
我凝神,用我全部的感知去“阅读”那凹凸的痕迹。
“他们被折叠进了第55张牌...”
血液,如果纸牌有的话,瞬间冲上了我的“头”。第55张?就是我们这副牌!就是这个躺在我身边的、表情暧昧不明的鬼牌!
几乎是那双一直闭着的、画出来的眼睛,猛地睁开了。没有瞳孔,只有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漩涡。它不是在看我,它是在吞噬光线,吞噬周围一切细微的声音。那咧到耳根的大嘴,弧度没有丝毫改变,但那份滑稽,此刻变成了纯粹的、令人胆寒的诡秘。
它知道。
它不仅知道那句话,它本身就是这句话的答案!所有的“8”,不是消失了,是被……“折叠”了?折叠是什么意思?压缩?囚禁?融合?
没等我从这巨大的惊骇中回过神来,那张鬼牌,它动了。不是被风吹动,不是被任何外力带动。是它自身,像一个活物,轻微地、慵懒地……翻了个面。
正面朝上。
月光直勾勾地照在它那张色彩斑斓、笑容癫狂的脸上。那笑容在月光下扭曲、放大,仿佛在无声地狂笑,嘲弄着我的发现,我的恐惧,我微不足道的存在。
然后,我听到了。
不是用耳朵,是直接响在我意识最深处的、被挤压得变形的、无数个声音叠加在一起的……
*救……命……*
声音来自鬼牌那咧开的、黑洞洞的嘴里。
不。
那不是嘴。
那是牢门。